那時候,我們都還小,我6歲,它6年;我們的性別一樣,我是個小女孩,它是只貓.長的皮毛又黑又亮,四個蹄子是白色的,嘴和鼻子還有下巴都是白色的,還有尾巴尖也是白色的,我弟叫它黑貓,我叫它黑亮,(據老輩講貓的壽命一年等于人得8年,也就是說貓48歲了,也等于老貓了)。。。。。。
也許有這麼多“相同之處”吧,它就成了我的老朋友。當然,我們要背著我的媽媽偷偷地交往,我總是趁媽媽上班的時候,雙手將它抱住,然后一溜煙兒跑回屋里的大炕上,我給它單獨弄了一些好吃的,例如:爸媽買的豬腸子準備過年吃,未洗干凈,春節前,在外面在楊木桿上凍掛著,我就一刀一刀地割下來,放在炕上慢慢緩著冰溜碴子 ,再喂貓,有時候,媽媽開小灶,改善生活,我就給它單獨弄了一些好吃的,就放在自己的小手心里,讓它的小嘴,勤勤地舔舔吃,然后,弟弟就摞積木給他看,他有時會看的出神,圓圓的大而黑亮的眼睛隨著弟弟動作而不停地轉動著,偶爾還會“喵喵”地叫兩聲,好像在叫好,也好像在提不同的意見。有時呆的無聊那時候,我弟弟就把它硬往它蓋得“房子”里塞,不小心碰到了支柱,“嘩”的一下塌方了,嚇的黑亮喵的一聲驚叫,險些跳起來,一下跳到我的懷里,仍有些驚魂未定而又莫寧奇妙地看著那一片狼藉“廢墟”。玩累了兩個弟弟就和黑貓黑亮一起睡覺,我弟經常把它摟在懷里,或者,我兩個弟弟平躺在炕上,然后把它放在心口窩上,在那帽子或者毛巾頭巾手絹之類的玩意兒一蓋,只露出它的大而圓的的黑腦袋,在弟弟因呼吸而起起伏伏的胸口,說它會睡得很香很甜,那種感覺好像我們小時候的搖籃里吧。有時我的弟弟醒了,它還睡著,偶爾瞇縫著眼,舔一下自己又黑又亮的毛,我感到一種及親切的被信賴、依賴的幸福。黑貓黑亮它長得很胖,比我們家以前養的貓都很胖很壯些。它的性格也比我們養的其它的貓和狗要好,我沒看到它和其它的貓狗打過架,這和我對它的:“溺愛”是分不開的,是不無關系的。 它的毛早已變成了烏黑錚亮,又黑又亮的皮毛開始有些硬了,大而有力的爪子抓我撓我和我嬉戲我已經感到了一些疼痛,它的腳趾也很有力,已經開始抓很多很多的耗子了。它 依舊和我及弟弟最好,放學時,看到我和弟弟打開院門,他就從房檐下來再跳到小倉房,再跳到院墻,再從梯子下來,在我和弟弟身上來回蹭,并歡快地沖我喵喵地叫兩聲,我和弟弟遇到這種情況情況下,會走到它身邊,伸出兩只手抱著它在院子跑兩圈兒,(只有它可以這樣輕易地被我和弟弟抱住),它開始越來越胖了,抱一會兒竟有些累了,邊撫摸它兩下,放下,飛跑屋去做那些似乎永遠也做不完的作業去了。那時,年少無知,帶的我倆個弟弟,一起作,真是作,到了快過年關了,爸媽開始洗腸子,煮熟以后就剩一碗了,為此,爸媽氣的沒少揍我。還有,那個在那個單調空乏而又貧瘠的年代,快過年了,真是太好了!我們小的時候是多麼盼著過年啊,媽媽為我買的新衣服、褲子、帽子、鞋、等等······還有很多好吃的,五顏六色的鞭炮,還有哧花炮,幾乎沒有人管我們玩耍,構成我們一年一度的“極樂”。進臘月門大人已開始熱火朝天地準備年貨,這其中一項就有屠殺淘汰一些自家養的家禽,這這其中就有雞鴨魚豬,而這樣屠宰的大事一般都由爸爸來做,并且都是爸爸獨立完成的。可這次爸爸竟;“求助”于我,他指著我的那只又大的又已經不在小的又黑的黑貓黑亮說:“孩子,它不是最聽你的嗎?幫爸爸捉住它,磚廠你肖叔叔借幾天捉耗子。”接到這個“命令”時,我正著急挨著家赴小朋友之約,參觀他們的新衣服,新鞋,帽子,手套,襪子……也沒多問,更沒多想,便跑到黑貓黑亮跟前。剛經歷完爸爸一次屠宰雞鴨鵝的“驚心動魄”抓捕的它下意識地躲了一下,但還是順從地讓我抱住了。也許它以為在我的懷里更安全、更可靠吧,在它的心里,我應該是比它強大強悍好多,足以能保護它吧,我心不在焉地抱著它往爸爸懷里一塞,便應著所謂的八仙女(兒時朋友有;百香,果香,劉榮,小茹,大民,大秋,詠梅,還有我,)的招呼“呼啦”地一下跑到院外去了。隱約地聽到絕望凄慘的家禽鳴叫聲,混在偶爾傍年關的年味鞭炮聲中,是似而非。
這一年的春節,和往年一樣的開心,,甚至一年比一年的更好。只有過年的時候才親自露一手的媽媽做的紅燒鯉魚,鴨,鵝,兔子肉,還有小雞燉蘑菇,黃花菜炒肉,蒜薹炒肉,西紅柿炒雞蛋······撐得我和弟弟的小肚子飽飽的都鼓起來了,快樂的日子總是那么難得而又短暫,如我們快樂童年的新年。
記得小時候,媽媽每年為我買紅色的,粉色的頭花,紅頭繩,那些上海知青,每年回家探親給我買五顏六色的發夾,還有粉色的長毛圍脖的頭巾,北京知青,給我買紅色的三角巾,記得那是三角菱形塊一個一個的堆積而成,樣子十分好看,記得小的時候,上學時同學十分羨慕,記得那時風靡一時,那時候到處顯能,心里美滋滋的,寧波青年,給我大弟弟買棕色的反毛皮鞋,夏天,我兩個弟弟從小喜歡捉魚摸蝦,由于怕把鞋弄臟了,就放小清河的河沿上,光忙著捉魚摸蝦去了,結果,被過路的人偷跑了,只好光著腳回家,路上被玻璃渣扎破了腳,記得那時候,去醫院縫針,結果到拆線的時候,曹培醫生說:“回家吧!不用拆線了,都找不到新線頭了,” 小時候兩個弟弟真是調皮,一天到晚在炕上嘻嘻哈哈,打打鬧鬧的,就是在炕上瘋搶,瘋鬧,傻乎乎的使勁頑皮。那年月,新鮮玩意兒少的可憐,寧波青年 ,曹繼亮叔叔給我小弟弟買的黑色的豬皮皮鞋,大弟弟不樂意,兩個搶,媽媽只好讓他們輪流穿,把我兩個弟弟高興的晚上睡覺都穿,四川青年,陳光輝也是我把這一輩子唯一的徒弟,也是我爸這一輩子最驕傲的徒弟,那時候條件十分艱苦,在上個世紀60年代,(1963年—1965年),城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,由于他們吃那時叫(火房)又叫食堂,靠的慌,沒油水,一整就上我家讓媽媽給他們改善生活,媽媽相當善良,純樸,做一手好菜,尤其具有山東人的美德,熱情,好客,好爽!想當年,很受他她們喜歡青睞,每年過年回家探親,回來以后,都給我和弟弟帶好吃的,例如:甘蔗,蠶豆、甘蔗糖、糖果,餅干之類的東西······哈爾濱青年,每年回家探親,都為我和兩個弟弟買衣服,褲子,記得小時候穿在身上花衣服,大粉紅格格衣服心理美滋滋,甜絲絲的,那個美啊!甭提有多高興啊!
年很快過去了,寒假也很快過去了,我又開始恢復了以往勞碌而緊張的學習生活,我繼續當我的小學生,繼續循規蹈矩按部就班地按時上學,上課、放學、做作業。而在有一天放學時,突然的就想起似乎已多日不見我的黑貓黑亮了。第二天、第三天依舊沒有看見。便心急火燎地問媽媽:咱家黑貓黑亮上哪去了,是不是丟了!”媽媽嚇了一跳,趕緊回家看看,“一看沒有丟啊!”沒丟?那我那只黑貓黑亮呢?”
“啊,可能你肖叔叔家抱走那一只吧?那是只母貓,老下崽,太煩人了。”
我想起來了,想起來了,我老向父母纏著要我的黑貓黑亮,媽媽沒辦法,只好去磚廠肖叔叔家要我的貓,媽媽回來說,:“磚廠的老廣叔叔(其實他姓梁,因為他是廣東人,所以人們叫他老廣)他們把它當成野貓打死吃肉了。”是我,是我這個它最親的“人”,害了它!我鼻子一酸,生氣地把書包摔在炕上,。我再沒有興趣去抱我家那些貓,甚至有一小段時間,不在養貓,不再親近小動物······
如今,小男孩已長成了大男人,小女孩也已經大女人,曾經認為是很傷痛的是,如今也不過成了模糊的記憶,‘‘為活”‘‘為生活所迫”而奔波的我又忙著打理生意,哪有那麼多的“閑心”去悲傷,去悲憫一只老貓的命運呢?但我每年過年還是記得它,并有一絲絲的愧疚與傷痛和傷感。
“黑貓黑亮你別見怪,自從你變成梁中心和肖墨水家的一刀菜”以后,每年爸爸媽媽還有大人們殺家禽殺雞鴨鵝兔子時‘‘念的詞兒”,小的時候我不懂事兒,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,曾把它當兒歌唱了很多年,甚至好久很久······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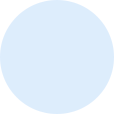
 武隆籍游客專屬福...
武隆籍游客專屬福... 2020重慶仙女山草原...
2020重慶仙女山草原... 到重慶武隆玩,這些...
到重慶武隆玩,這些... 真正的南國牧原!仙...
真正的南國牧原!仙...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