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個彤云密布的下午,十多歲的黃黃遠遠地搖著尾巴把我接進了墻皮剝落的紅瓦老屋。
幽靜的院子相隔十年清凈如故,只是沒了母親忙碌的身影。還是那張八仙桌,還是那口座鐘,還有那盤縈繞在夢中的溫暖土炕。
眼下父親熬過一劫,身體虛弱,平時都是姐妹照顧,這次,我終于狠下心,推了手頭工作,請假回來權且盡盡孝心。
父親整個身子埋在厚厚的棉被里,灰白的頭發顯得有些凌亂,瘦削的臉上,眼眶深陷,兩眼無神。乍見到我,說不上是意外還是驚喜,眼里閃著亮亮的光,抓著我的手不停地問這問那。
姐姐抱怨說,爸很久沒說這么多話了,都留著和兒子說了,連這個都偏心。父親笑了,眉頭上的皺紋舒展了些。
父親的手透著涼意,無力地抓著我的手,生怕我再像當年突然離去,我兩手緊緊捧著它,一如兒時怕我走失緊牽我的手。
黃黃搖著尾巴跑進來了,用腦袋蹭我的褲腳。父親說,狗通人性,這么多年了,還認你,準是還記得你喂過它哩……看,也老了,唉。父親長長嘆一口氣。
我明白這無言的嘆息,當年麻雀般嘰喳亂叫的一屋人,轉眼剩他孑然一身,年老體病,豈不孤苦。我聽出這嘆息里有無言的責備,太多的無奈。我無言以對,任憑珠淚在眼窩里打轉。
下雪了,紛紛揚揚,晚飯后,才停下,天地間一片白。狗躲進窩棚,四下里一片靜。老式座鐘慢吞吞地敲了六下,我詫異它慢了一個小時。父親笑了,慢也有慢的好處,天晚了你還覺得才傍黑(才黑天)呢,省的眨眼一天,就又過年了。我仔細品味父親的話,似乎也有道理。我熄了燈,和父親一炕,擁被而坐。
談起孩子,父親一下子變成了婆婆嘴。話題由孫子自然轉到我身上。我小時候淘氣,把三大娘家抱窩雞的翅子扎起來,結果小雞沒孵全;爬樹捋榆錢時褲襠被刮了個洞,拿手捂上;到灣里滑冰漏進冰洞,一夜烘烤,卻烤糊了棉鞋……
月掛枝頭,雪映寒窗。黑暗漸漸退去,陳設的輪廓慢慢浮出:棗紅的八仙桌,老式的座鐘,醬紫的南泥壺,還有這盤仿佛與生俱來的土炕。時光倒流,往事如煙。吃完喜酒,祖母會踮著小腳趕來,酡紅色臉,從大襟褂里抖抖地掏出糖塊塞在我嘴里,我卻把她的綁腿布藏起,害的她呵呵地笑罵;母親整日奔忙在田間地頭,獨輪車就是我和妹妹幸福的搖籃;冬日晨風凜冽,炕頭卻燒得暖暖,三個孩子雛燕似的縮在被窩里吃燒熟的地瓜片……
父親在喃喃自語中沉沉睡去。忽然想起兩句詩:“想得家中夜深坐,還應說著遠行人。”淚眼朦朧中,仿佛看到父親無數次夜深獨臥輾轉思親,我披衣下炕,走出門外。
月亮明鏡高懸,灑下一片清輝,天地純然一色,清新干凈;天空幽藍深邃,幾顆星星一眨一眨,天際處,移動的一點紅光留下神秘的玄想;高高的東廂房投下大塊的黑影,仿佛白底上一朵暗花;南屋頂積雪映著月光,發出搶眼的白;棲息的鳥雀偶爾碰落樹上一兩簇積雪,粉末飛揚,絲絲點點晶瑩閃亮;空氣潤濕清冷,有雪的味道;黃黃靜臥草棚,不聲不響,遠處傳來一兩聲咬,是狗夢中的囈語抑或對親人的呼喚,沒有風,耳朵里一片虛靜,恍然回到創世之初。
我入定般沉浸在這片夢幻色的月光雪境里,獨享她的靜謐,驛動的心終于找到了棲息的港灣,慢慢咀嚼潮水般涌現的往事,簡潔美妙,恬淡純凈,心中那一方柔弱處溢滿親情。回想昨日打拼,如隔世般遙遠,似一個朦朧的夢。穿行在都市的森林里,摸爬滾打,求學求業,結婚生子,小房換大房,還車貸還房貸,快速運轉的列車,剎不住慣性的車輪;步履匆匆,來不及欣賞路邊美景;快餐式的節奏,也無暇品嘗生活的真味。
“錢是永遠掙不完的,路要一天天走,日子要一天天地過。”父親說。是的,在追逐金錢物欲的路上,我曾一度迷失自我,誤以為掙大錢就是給親人最大的榮光,忽略了真情淡漠了親情,母親早已過世,陰陽兩隔,欲養不待,何其痛哉!父病多年,我何曾床前盡孝。
初愈后的父親,吃東西細嚼慢咽,走路也慢慢吞吞。我似乎禪悟了一點:生活需要細品慢嚼,親情更需要細細滋潤。
旭日東升,廣袤原野蒼茫無垠。雪地上,一深一淺,兩行腳印,伸向遠處。父親破天荒地圍上那條紫紅圍巾,挽著我的臂膀,慢慢走著,一如兒時我被他大手牽著。
漫步在雪白的大地上,身心一陣輕松愉悅,我渴望這樣慢慢走著,走到天老地荒。遠處,天地相接,潔白如云,親情純凈如雪。
作者簡介:靳順高,男,中學教師,發表小說、散文、詩歌等幾十篇(首)。2013年,獲全國“交運杯”微型小說征文三等獎等。2014年先后獲得全國首屆“夢之路”征文二等獎等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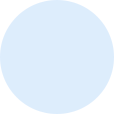
 武隆籍游客專屬福...
武隆籍游客專屬福... 2020重慶仙女山草原...
2020重慶仙女山草原... 到重慶武隆玩,這些...
到重慶武隆玩,這些... 真正的南國牧原!仙...
真正的南國牧原!仙...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