父親是個農民,一生躬耕于貧瘠的土地,直到生病住院的前一天,還在田疇里揮灑著汗水。他粗糙的手里,大多時候抓握著拙樸的農具,很少拿著纖細的筆。可是,他寫得一手好文章,他務農,是時代結出的一枚澀果。他因家庭出身不好,初中畢業后,學校就勸他退學了。去年7月,父親住院檢查,是肺癌晚期。僅隔半年,他就匆匆地走了,永遠離開了我們。
父親的那本日記,只有薄薄的幾十頁,我發現它,是在整理父親遺物的時候。我的父親啊,在人生即將凋謝的時候,拿起了久違的筆。
父親在合肥住院,我和弟弟一起陪伴著他。在此之前,我帶他在區醫院檢查了,我們都知道病情不容樂觀,是我們家庭一道難以逾越的坎兒。
確診需要做纖維鏡檢查,父親原先健壯的身體,已被病魔侵蝕得虛弱不堪,他血凝素低,剛住院的十來天,需要輸液增加血凝素。那時他每天的醫療費用,在一千元以上,這是父親一季農作物的收入,也相當于我們兄弟兩人半月的工資。我們在醫院的附近找了家價格便宜的小飯店,為了給父親增加營養,每餐都炒一個葷菜,可他很少動箸,我們給他夾菜,他說:“你們吃,你們吃,我吃不了多少。”晚上,我和弟弟等父親睡下,就悄悄離開病房,到樓梯上坐下,抽著煙商量第二天的安排,或者望著晦暗的樓頂發呆。
我們每次出去,父親并沒有睡熟,等我們走了,他就打開床頭燈,寫著日記。父親的第一篇日記寫的就是那時的事情,日記的最后,他寫道:“如果是癌癥,我不會治療了。稼穡艱辛,不能讓存蘭(我母親)的血汗錢打了水漂。孩子們也有自己的負擔,不能拖累了他們。”
父親做纖維鏡檢查后,大出血,他劇烈咳嗽,臉色蒼白,神情痛苦,整個下午一口一口的鮮血接連從口中吐出,接血的瓷缸每過一會就盛滿了。我和弟弟實在控制不住悲傷,當一人在他身邊時,另一人就躲到醫院的走廊里失聲痛哭。
父親在日記上寫道:“今天大出血,把兩個孩子嚇壞了。他們從外面進來,眼睛都紅腫著,他們沒有經歷過這樣的恐怖的事啊!”字里行間沒有一字提及自己的痛苦。在那樣一個倍受煎熬的時刻,生命的燭火隨風搖曳,可他顧及的只是我們的感受。
檢查確診后,醫生告訴我,父親已錯過最佳的治療時機,無藥可醫了,我和弟弟為我們的大意自責愧疚。我們給父親辦理了出院手續,把醫生開的藥,換裝在治療肺炎的藥瓶里,對父親隱瞞著的病情,只告訴他是肺炎,休養一下就沒事了。每個周日,我會回家看望父親,我問他身體狀況,他總是笑著說,吃了我們買的藥,好了許多。他還說現在沒事了,不需要我每周回去,要我自己注意休息。其實,他日漸消瘦,挺拔的腰身在慢慢佝僂。
姐姐后來告訴我,父親那時最高興的,就是我回家,陪著他聊天,可他擔心耽誤了我的工作。父親的一篇日記寫著:“這幾天一點東西吃不下,痰中有血,后背也疼得厲害了,是癌細胞轉移了吧。大概,死神在不遠處招手了。孩子們知道了,會很著急的,他們工作都很緊張啊!”
2010年12月13日,父親去世了,按鄉下風俗,人走了要停放在家里三天。那三天兩夜,我只是在沙發上打了一會兒的盹兒,其余的時間都坐在父親的身邊。父親放飛我快二十年了,我和他如兩個圓心、半徑都不同的圓,劃著各自的軌跡,很少交集,像這樣在深夜近距離地相伴,極其稀少。遺像上的父親正對我笑著,我的淚時不時就噴涌出來。父愛不存,背后少了一雙殷切關注我的眼,我感覺一切都失去了色彩,變成灰白的了。埋葬了父親,我失魂落魄。
就在那時,我發現了那本日記,最后一篇日記是留給我的,那字跡已模糊不清,我知道父親在寫它們時,用盡了全身的力氣。日記中,父親要我對他的離去不要太悲傷,要盡到一個長子的責任,照顧好母親,與弟弟一生和睦,此外要將兒子教育好,“青出于藍而勝于藍”。那刻,我麻木的心驟然清醒,是的,父親走了,生活還得繼續,責任仍要擔當。如今我們陰陽兩隔,可他并沒有遠離我,畢竟,我的血管里流著他的血液,性格里烙下了他的影子,他看似遙在天涯,那濃濃的愛卻就在我的身邊。
父親的日記,文字簡約、質樸,可我看到那文字后涌動著滔天的情感巨瀾,它是父親在生命彌留之際,用愛燃起的一堆篝火,它映亮了我生命里寒冷的夜晚,將焐熱我今后所有的歲月。(1658字)
作者簡介:朱迎兵,1974年3月生,本科學歷,《讀者》、《特別關注》等雜志簽約作家,安徽省散文家協會會員,有100余萬字的教學類文章和文學作品散見于各類報刊,并有小說在全國獲獎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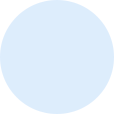
 武隆籍游客專屬福...
武隆籍游客專屬福... 2020重慶仙女山草原...
2020重慶仙女山草原... 到重慶武隆玩,這些...
到重慶武隆玩,這些... 真正的南國牧原!仙...
真正的南國牧原!仙...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