燃著煙,與澹然少語端著旱煙袋年邁的父親對面坐著,靜靜地看著臉上刻著滿是歲月印痕老父親的從容,最是我自如的時段。
父親幾乎經歷過了上個世紀中國所經歷過的所有災難,只是到了晚年,才換得了安寧的時光。兒孫雖繞膝,卻仍不停的勞作,苦難已使得他從不知道什么叫作勞累。
花甲之時,把他最小的兒子送出了山坳里的村莊,擺脫了與泥土和石塊的糾纏。在這之前的二十多年前,也曾送走出兩位,曾經的優秀終被不逢時的節氣所錯遇,并又一一回到了原先生于斯長于斯的土地上。雖然家鄉的山水風物在國中也算作上乘,當幾經失落的磨難而自鄉郵所得著了通知書時,他只是若有所無似的應了一聲,“哦,走了。”
十多年在外,先前回家是很勤的,娘總是說隔上一段時間,覺著要回來了而未見著便想得慌。家鄉的電話也是農話中較早開通的,因而就有了延宕歸期的借口。終于,有一次回到家時,父親說:“我準備就要到你那里去看看你了。”諸事煩擾,心不能靜,又生懶散,間隔稍長,亦多是有歉疚意,心里似乎覺得欠了什么似的。
坐著面對父親時,總喜歡聽他說那簡短的話語——這樣“好”,那樣“不好”。
歲月不駐,父親雖還硬朗,但也蒼老著。
近些年,父親每從侄輩們口中得知去了省城,偶或赴京滬等地參加學習或交流研討及展出的事兒,見著了總會問上一聲“又上南京了”,“去合肥了”。
“努力著”,時常輕輕地這樣對自己說,因為我知道我是您平靜面孔里無聲的念叨。
如今,回家,若是再想見著他,——能面對的只是百年老屋后面家山南坡那一抔去歲的新土了。慎終追遠,是他孩提時私塾里的記憶,在我又端是那堪的回憶……
貢家新 1969年9月,男,安徽懷遠縣財政局。政治學研究生畢業,省政治學會理事,省書法家協會會員、作家協會員,市作協理事及小說、詩歌創作專委會副主任,市硬筆書協副主席。以小品文見長,并對傳統文化的研習多有專注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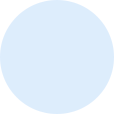
 武隆籍游客專屬福...
武隆籍游客專屬福... 2020重慶仙女山草原...
2020重慶仙女山草原... 到重慶武隆玩,這些...
到重慶武隆玩,這些... 真正的南國牧原!仙...
真正的南國牧原!仙...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