記得那年我14歲,剛上小學五年級。
是個麥季的下午。
放麥假了,我們一群小學生在本村一位女老師的組織下,幫生產隊拾麥子,
午后的太陽,明晃晃毒辣辣,鑠石流金。一踏進地里,一股熱浪猛地撲面而來,我一陣眩暈,忙又縮回到地頭那棵大桑樹下的濃蔭里,悠哉游哉了整整一個下午。
下午收工了,小朋友們都撅著小屁股,吃力的背著大捆的麥子,往回走。只有我,用一根長長的繩子捆著一小把麥子,粗如兒臂,懶洋洋,訕訕然,低著頭跟在隊伍后面。
這難堪的景象,讓在場上干活的母親盡收眼底。母親是個干活不要命、極要面子的人,在生產隊里,她是唯一能和男勞力抗衡的婦女。無疑,兒子的懶惰窩囊,讓這位女強人蒙受了奇恥大辱,她一言未發,猛地沖上來,奪過我手中的繩子,朝我劈頭蓋臉的狠命抽打,直打得我滿地滾爬,沒命嚎叫。隨后,她又用繩子一下子勒在了我的脖子上,我一陣窒息,眼冒金星,兩耳轟鳴。母親隨即被人拉開,兀自怒氣未消,嘴唇青紫,雙手顫抖不已。我呆住了,由慚而驚,驚而怒,繼而化為歇斯底里的刻毒辱罵—— 地主老婆子欺負窮人,打倒地富反壞右!我知道母親娘家出身地主,便把她的大忌諱致命傷,化作滾滾污水,向她迎面潑去。聽到兒子的咒罵聲,母親身體輕輕搖晃了一下,接著便垂首肅立,觳觫汗下,臉色慘白,宛如一只斗敗了的公雞。我感到了一種恥雪仇報的莫大快感。
那天晚上,我沒回家,我在一個白天都讓我驚恐萬狀的柴禾園里坐了一夜。我和母親徹底的記了仇,母子間猶如荒漠一般,直到如今。
不知不覺,三十年過去了。
那一天,我那上小學的孩子拿著一張補考通知單,嬉皮笑臉的遞給了我,我接過一看,當時我那個氣啊,頓時渾身冰涼,手腳發麻,嘴唇青紫,眼冒金星,大腦一片空白。雖然我深知失敗者不該橫加責罰,但我還是將拳頭握緊了松開,松開了又握緊,我把補考通知單扔在桌上,未置一個可否,便掄個風,轉身進了臥室,點上一只悶煙,獨自向隅而氣。
驀地,我想起了二十年前和母親的那場沖突,我豁然弄懂了母親當時的心思。
是啊,母親識字不多,她不會用娓娓的語言,深入淺出的闡述人生哲理,她只會用近乎殘酷的行為警示自己的兒子,你是農民的兒子,就必須好好勞動,全力勞動,拼命勞動。因為勞動是一個人生存的前提,立身的根本,人格的外化。
時間啊,多像大慈大悲的菩薩,清水一灑,點化愚蒙,開我混沌。
哦,霹靂與雨露,一例是春風啊。

 門票預訂
門票預訂 武隆景區微信
武隆景區微信 武隆景區抖音
武隆景區抖音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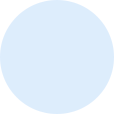
 武隆籍游客專屬福...
武隆籍游客專屬福... 2020重慶仙女山草原...
2020重慶仙女山草原... 到重慶武隆玩,這些...
到重慶武隆玩,這些... 真正的南國牧原!仙...
真正的南國牧原!仙...



